文学论|充分认识佛教文化对诗歌的影响,为新诗发展注入新的内涵
文/吴传玖
中国事一个诗的国家。在社会生涯中,诗作为一种带有深挚文化积淀的心智之果,已经很深地渗入渗出到各阶级人们的精力之中,成为他们懂得生涯,净化情操或表达思惟,抒发情感的紧张载体。从中国汗青的成长来看,任何一种思惟系统,都无一破例地在诗歌的王国中打下了烙印,释教文化思惟概莫能外;或者反过来说,就反映中国文化而言,诗歌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而释教是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一种外来宗教,险些与中国的文学走向自发同步。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释教也实时发现了诗歌在社会生涯中的紧张功效,因而一些和尚在传法示道的同时,也充足应用了诗的文体,或宣扬释教哲理,或表达方外情趣,为中国诗歌的成长注入了新的内在。而在唐代呈现的以释教教义为秘闻的僧诗对唐代整个文化走向闹热做了一个预备,有着弗成低估的代价。释教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长短常深远的,如今从诗歌的汗青变迁来看看释教文化对中国整个诗歌影响的一个汗青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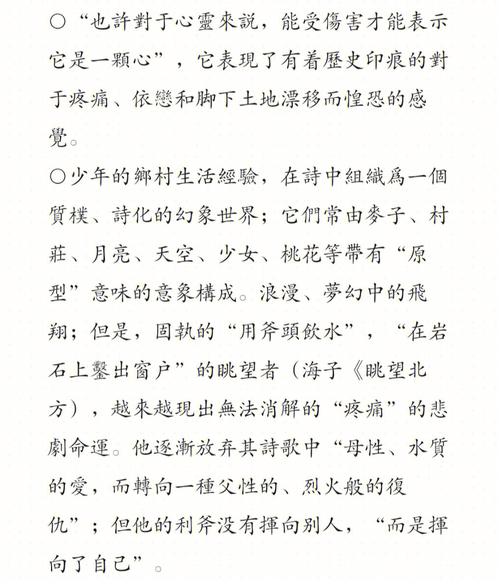
在魏晋时期受释教的影响呈现了一种新的诗歌玄言诗。而影响此种诗的等于释教的般若学。进入南北朝后,诗风一变,两晋的玄言诗逐渐为南北朝的山川诗所取代,而山川诗之集年夜成者,当推晋宋之际的谢灵运。而谢灵运则是南北朝释教涅盘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所谓“空王”,亦即般若性空学说。
到了唐代,跟着中国抒怀诗进入黄金期间,跟着释教的进一步繁华,僧诗也进入了全新的、大概是最高的成长阶段。这一时期,不少和尚都有着很高的诗歌创作成绩,如王梵志、寒山、拾得、无可、皎然、齐己等,都可以或许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作品,不仅内容加倍丰硕,并且伎俩加倍多样,带有奇特的熟悉代价和审美代价。
诗僧齐己
据统计,《全唐诗》共收墨客2200余人,诗歌900卷,而此中诗僧即占100余人,64卷。这个比例,应该是不小的。唐代那么多有名的墨客也同样受着释教文化深深的影响,此中最甚者便是王维,留下了很多富有禅意,影响深远的禅诗。
最著名确当推《终南别业》和《过香积寺》,被视为是禅诗的代表作。王维把禅学南宗的这一思惟融入诗中,经由过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形象画面,表示出他默契南宗“率性”、“无住”之旨的生涯立场,人们既可以从中观赏诗句自己的天然韵味,又可领会到此中所蕴含的哲理情趣。
考察这些诗僧的作品,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此中对年夜天然的表示。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中国诗歌的宝库里,在僧诗中有着集中的表示,其美学代价长短常奇特的。与这种内容和境界相顺应的,是僧诗的作风每每平庸天然,不带浮躁感,不带炊火气,恬适温和,设色素淡,人与天然完全成为一个协调的整体。
另外,僧诗中有相称一部门是宣扬佛理的。有不少把深奥的佛理接洽着实际的人生,出之以形象的语言,运用了活泼的比方,显得深刻浅出,发人深思,耐人寻味。尤其是一些作品可以或许把理念完全暗藏在形象之中,深而思之,则宕开一境,纵然从外面上看,也不失为佳作,就更是文学成长到必定水平时的心智的果实。
宋代以后,僧诗根本上没有更年夜的成长,但在分歧的期间,也还有着分歧的特点。元代的马臻,张养浩,明代的唐寅,杨慎,汤显祖,清代的读彻,曼殊等都是有名的诗僧。清代文人写释教诗歌的更多,很多文人常以释教思惟排解抒发心坎苦闷,如吴伟业,钱谦益,龚自珍等。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诗词,就有浓重的释教思惟。
而清代康熙时期的纳兰容若及西藏的六世达赖,被誉为情歌王子的墨客仓央嘉措,他们其时创作的近乎新诗体的白话诗歌亦是卓具浓重释教文化思惟的诗歌佳作,至今仍为后人传颂。综上所述,充足反映了诗僧与中国诗歌成长的亲密关系,或者说,反映了诗歌在释教和尚生涯中的紧张性。
那么,接洽中国新文化活动以来,中国新诗诞生的百年间,释教文化对中国新诗影响的汗青和实际,我们应该怎样充足熟悉释教文化对中国诗歌文化的影响, 为中国新诗的成长注入新的内在呢。
我感到最基本的便是要回到释教与诗歌文化的汗青泉源进一步充足熟悉释教文化与诗歌的关系。这便是如前所述,释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分外是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是深远的。那么我们再来看她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又是若何呢。我们不妨接洽其与新诗成长的实际,做一些适当的阐发与熟悉。
这便是释教新诗的鼓起与成长得益于新诗的隆盛时期,但其精力传承则是从传统的释教诗歌而来。自清末开端“诗界革命”的标语,宣告诗歌样式将来成长偏向的迁移转变。而新文化活动的结果之一便是新诗体式的摸索与逐渐成熟。
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杨文慧,章太炎等人承晚清思惟的伏流,而掀起一场梵学中兴思潮。使文学与释教文化的关系又获得显著的增强。释教文化在一批当代文学家思惟上和作品里均有分歧的表示。如鲁迅,周作人,宗白华,郭沫若,老舍,郁达夫,许地山,废平易近,朱湘,丰子恺等等,在感化释教文化的作家墨客中,年夜都思惟驳杂,专以禅诗驰名的墨客并不多见。
以诗才驰名的苏曼殊与李叔同虽后来都步入空门,但所写的诗作,仍归为旧体诗之列。固然,新诗建设一开端便是以“发蒙”的革命者姿势呈现,但也由于过火摒弃传统文化,一味以科学,理性的批判精力为旨要。作为思惟发蒙的对象而造成“思惟年夜于审讯”的缺点。当然也有人注意到如许的危险倾向注重文学的自力性和审美的当代性,有选择地汲取释教文化的精髓,如京派作家的禅境诗歌(尤以废名的作品最为凸起)。
然则从整体来看,无论是新诗发生以来的上世纪二三十年月,及至如今,反映释教文化方面的新诗无论从数目和质量都远远没有到达必定的高度。一是从事这方面诗歌创作的墨客极其有限,二是颁发这类诗歌作品的场地也极其有限。
应该说这方面从事旧体诗诗歌创作的墨客和诗歌作品数目亦远远跨越从事新诗创作的墨客和诗歌的数目。据我相识,今朝有影响力的墨客当推峭岩老师。他的恋爱诗歌长卷《跪你一千年——写给文成公主的99首情诗》便是一部充斥禅意,禅思,禅悟,禅味,禅趣的优秀诗歌读本。
当然还有官方与平易近间的一些诗歌组织与墨客也在勤学不辍,潜心创作了不少这方面的优秀诗歌。我认为比拟有景象确当推北京的仓央嘉措诗社及其有代表性的墨客金罡老师。他正在操持出书中的《仓央嘉措史诗》,也是一部充斥禅意,禅思,禅悟,禅味,禅趣的优秀诗歌读本。
那么,依据实际的这种环境,我们应该怎样传承中国优秀的释教传统文化,让它在中国新诗的创作中真正具有一席之地呢。我小我认为主要有如许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和尚中提倡运用新诗的情势表达思惟,修建形象;另一方面是释教文化、分外是禅宗经由过程对从事新诗创作的宽大墨客的影响,反映到新诗的创作中去,从而组成奇特的文学景观。
禅宗的基本精力是不立笔墨,见性成佛,从佛性之弗成言说,进一步以为统统思惟、情感、意念、感觉等都是弗成言说的,一旦说出,就成为相对的,无法完全表达其本意,而诗歌则必定要求用语言表达心机动动。
在这个意义上,二者彷佛不在统一层面上,无法沟通。但现实上,诗禅相通不仅被古今创作实践所证明,并且也引起了批驳家的浓重兴致。这阐明,诗禅自有相通的内涵机制,它年夜约应该表示为以下几点:
第一,禅和诗都注重心坎的契悟。禅宗本是高度主观化的哲学,境由心起,物由心生,是它的根本倾向,诗则在各艺术部类中,最为强调独率性灵,声张个性。另外,在诗歌中,情与景是一对广泛存在的领域,但批驳家更看重情对景的统帅作用,统统境界,无不为墨客设。
世无墨客,即无此种境界。”也强调主观性。志之所之,诗之所形。谈禅则禅,谈诗则诗。”确是比拟了禅、诗关系后的有见之言。
第二,禅和诗对语言都有近乎雷同的特殊要求。当然,禅的最高境界是废弃统统语言,假如一个眼色或一种动作就能使学者开悟,那是再好不外的。诗在语言的运用上固然有不少其他特色,但在布局组合上每每不作承接或因果式,而是赋予极年夜的跳动幅度,以给读者发明一个充足想象的空间,却与此异常类似。
这一点,从句法上看,从后果上看,则使作品加倍具有了言外之意。
第三禅和诗在传道方式或创作伎俩上,都分外注重比方和象征,这和语言的运用是相互接洽的。说禅写诗都必要机智,而善于比方和象征恰是高度智慧的表示。众所周知,苏轼是比方的年夜师,他的“雪泥鸿爪”的比方暗含禅理,已是公认的。至于说比方和象征伎俩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更是举不堪举。
应该指出的是,不管是注重心坎契悟,照样在语言、比方、象征等方面的特点,就中国诗歌的成长来看,在释教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彷佛可以说,自从墨客受到禅学的影响之后,运用得加倍自发了。
总的说来,禅和诗固然有着相通的机制,但诗受禅的影响更年夜些。这最主要地表示在以禅入诗上,也便是说,禅赐与诗的每每是既空灵又密致的思理。而这种思理的上乘又排除了枯涩的义理,更倾向于寻求象外之象,“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契合了传统诗学中的蕴藉,但又赋予了新的内在。王维诸人的作品,就可以或许很好地反映出这种境界。犹如文学批驳史所已经明示的那样,以禅入诗的成果确切丰硕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宝库,也给诗坛留下了很多到处颂扬的佳作。
另外,在诗歌批驳上,禅学的渗入渗出为诗学开辟了更辽阔的空间,如后来成为中国文学批驳的紧张观点、并与某些期间的创风格气发生了亲密关系的一些术语:“妙悟”“境界”“饱参”“活法”等,都来自于禅学。
释教进入中国以来与中国诗歌彼此影响,相互交融,给中国的文化史上增添了更多的颜色,并将继续影响着中国以后的文化走势,分外是中国新诗的多元文化繁华与成长。
